如何打造下一個情緒?
這是探索情緒與感受的第三篇,第一篇討論切身之痛的焦慮、並延伸焦慮的議題,在第二篇探索從心理安全感的環境,看焦慮這件事。從前兩篇的視角中,初探了情緒跟認知的相互複雜
而在一生綿延的情緒流中,我開始好奇更底層的情緒運作邏輯,關於這條情緒河流是怎麼運作?我們終其一身的經驗源自哪裡?
我們怎麼解讀這個世界?
我已經習慣社群媒體上,相同的社會事件各自表述;但即便是同一群體經歷相同事件,也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理解。
我時常納悶,這世界有沒有所謂的「真實」?的確,蘋果從樹上落下、太陽從東邊升起,但正如哲學問題「假如一棵樹在森林倒下而沒有人在附近聽見,它有沒有發出聲音?」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樹是否倒下,而是我們能不能注意並理解它。
那我們怎麼注意並理解事物?過去我以為,自己像進階版帕夫洛夫的狗,大腦只是反應刺激,但其實注意和理解始於經驗、語言的預測。
大腦隨時在進行預測:從一片綠色紡錐形薄片、預測是一片「葉子」再推測旁邊會出現的細長淡綠連結「枝芽」、進而到灰棕色、硬挺聳直的「樹幹」。
以上各個「字眼」都是概念,透過概念將各種綠、棕、紡錐形、橢圓形薄片都總結成「葉子」,概念,是大腦總結經驗的方式。而有了概念,我們才知道接下來要注意什麼。
等等,這難道是我們全都活在一場夢中,像是缸中之腦的懷疑論嗎?並不是,大腦會依照真實的刺激調整預測。
例如:大腦預測葉子旁有枝芽,實際注意並比較後,卻出現金屬色、彎折「鐵絲」與預測不符。鐵絲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,大腦會好奇「這是什麼?」。根據比對調整後續預測,將延伸的樹幹調整為「綁了鐵絲調整生長方向的樹幹」修正對世界的理解。
這種預測、刺激、修正的模式便是預測迴路(Prediction Loop),與傳統觀點「大腦接受刺激並反應」的差異在於,一開始的概念預測,已決定接下來會注意什麼。
這不像經典心理學實驗,要你計算一群人互相傳球時,白衣人傳球幾次,而你卻忽略中間走過一隻突兀的黑猩猩,無須特別專注,平常也會自然發生。
而迴路都在毫秒之間綿延不絕,只能透過特殊設計的實驗揭示部分特性。比如我很喜歡《How Emotion Are Made》裡的「經驗盲區」實驗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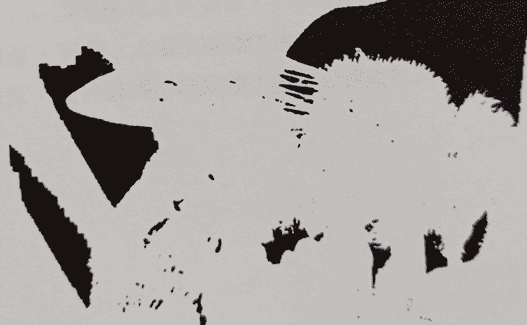
看著上圖斑點,若缺乏相關經驗形成概念,大腦也只能當這張圖是一張噪點。但只要你翻到文末、概念形成,突然間噪點就有了意義,而在生活中也能注意。
這種預測、刺激、比較與修正的迴路,使人產生擁有「自由意志」的錯覺,我們更像是裝著 LLM 的 Optimus。但我卻認為這是一件極其浪漫的事,人模擬了一生何其虛無,卻從中經驗活著,成就對當事人的浩瀚。能感受到浪漫這件事,正是其浪漫所在。
Love loves to love Love.
— Ulysses
而前文提到,大腦用經驗總結的概念預測,透過外側刺激修正,再產生下一個迴圈。那麼這些概念存在哪裡?大腦又如何執行這個抽象流程?
過去我認為,這些都是記憶,而記憶是回想時產生的朦朧場景,又或是所有智識跟技能的集合,這一切有個大腦倉庫,將其分門別類存放起來。
但《Why We Remember》提到:「回想過去並不是重新激起無數固定、毫無生氣且碎片般的痕跡,而是依靠想像力加以重建。」大腦並沒有單一存放記憶的地方,而是複數腦區負責不同程度的記憶,且彼此串連,讓我們有不同完成度的記憶體驗。例如,鼻周皮質負責索引 1,前額葉皮質負責概念的形成與補全 2,而我們耳熟能詳的海馬迴則負責提供場景 3。
在探索此機制時,我常以為能一步步感知運作細節,但這些細節實際超出意識所及。可以認知的,都已經化為意義。
情緒多樣性:結合身體內部的預測迴路
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
— Raymond Carver
剛才說的都是身體外面的事,那我們體內又是如何呢?
前文以葉子為例,解釋了多個腦區如何透過記憶執行預測迴圈。同樣地,體內也有川流不息的刺激正在發生,例如:前一篇 怎麼創造安全感?中提到的迷走神經,也是其中一個路徑,接受著來自身體內臟器官的刺激。
沒有概念時,身體的刺激只能被區分為強弱或正負,甚至像上圖的噪點難以察覺。但透過預測迴路,刺激被賦予了概念,這些刺激經驗就變成平常說的情緒。
這推翻了以往認為情緒有普遍定義的觀點,例如:嘴角下垂就必定是生氣、特定腦區反應必定是開心。但種種實驗證明,無論透過臉部肌電或 MRI 都找不到普遍性的情緒定義。
相反地,當大腦在預測時選擇了特定情緒概念,身體根據概念調整生理狀態。例如,使用「傷感」作為概念預測一片葉子的掉落,身體可能會放緩心跳、放鬆肌肉、但胃部輕微收縮。
在「傷感」的情緒概念下,我們更容易注意到體內「平靜又糾結」的感受。最後,大腦將情境與內部感受結合,完整了「傷感」的情緒體驗。
不過這並不是說能活成不死軍團:隨時隨地跟隨預測、積極快樂、至死方休。受限於身體預算(如疲勞、能量不足)我們會傾向以最熟悉、省力的模式去預測,無法時時以細緻概念處理情境。
怎麼重塑預測,以創造下一個情緒?
大腦預測迴路從外而內,透過情緒概念整合感覺、調用體內資源,創造源源不絕情緒經驗。而人也只能意識到,自己感知被概念化的經驗結果。
良好的飲食、睡眠與運動是良好體內感覺的原料,如果身體自我感覺良好,大腦便難以預測出負面的情緒概念。除此之外,有兩個方向是比較少提及而我想嘗試的:
敘說更精確的感受
在《How Emotion Are Made》中,特別強調了「情緒顆粒度」。每一次描述感受的時候,都可以更精確地選擇概念,讓大腦逐步細緻應對。試想,一件令人咬牙切齒的事與憤憤不平的事,兩者情緒概念下身體應對有所不同。但如果都歸類在生氣,身體就只能一概而論了。
而把一件客觀事實前後因果關係有條理精確的說清楚,是相對直覺的。如果在難以衡量的瞬息萬變當下中,怎麼嘗試更精確地描述呢?以一個有感而發為例:
前陣子看了一支公視的影片,片中主角一家過著儉樸快樂的生活,當時看完我覺得這樣的生活很美。
但我總覺得不夠:「只有美嗎?」細想了一下,確實不盡相同。這並不是一種敬畏或摒息的感受,還有一點點羨慕在裡面。所以又進一步定義為「牙癢的美」。但還是不夠,羨慕,也並不是單純想要,因為我覺得我沒辦法過上一樣的生活,最後記錄下:「牙癢的美,可及卻又自己不行的美。」
精確,來自頑固且挑剔地去選擇,選擇那些你想要的、更準確的概念。尤其不放過那些難言時刻,像是「該怎麼說呢?」「就像 xxx 的感覺,你懂嗎?」「是這樣嗎?」等話語卡在舌尖、心裡一堵的瞬間。在完全主觀的內在世界中,是無法得出一段文字等同於該瞬間的等式,只能冥頑不靈地趨近理想與感受的混合。
除了對選擇的執著,還需網羅更多概念,可以從人、文字、創作4甚至不同語言5。呼應近期推友 K 先生的推中敘述:「讀好的文字,特別要讀虛構。增加自己的詞彙量,就不會受限於單一而且低解析度的世界觀。」例如,「美」這個用字,就是來自於前陣子聽 電扶梯走左邊 with Jacky (Left Side Escalator #141 胡程維 的訪談,而覺得可以進一步用在更多場合裡。
我相信,固執且挑剔的選擇、精巧又執著地汲取概念,可以打造下一個更好,亦即更適切的情緒經驗。
回想對過去的新情緒
除了未來還未發生的情緒,我們也可以透過回想來重建已經發生的情境中,我們所擁有的情緒。
在《The Body Keeps the Score》中舉了非常多透過重述故事來走出創傷的案例:「當創傷令我們驚愕失聲,要想走出去,便必須以文字鋪設通道,細心收集散落的片斷,直到故事的面貌完整浮現。」
還記得海馬迴提供場景、前額葉皮質補充概念嗎?每次回想都是兩者共同建構新記憶的過程。我們只要在回想時多加一些新概念,未來便更容易出現期望中的預測。
例如:思考一個困難問題時,大腦會因燃燒葡萄糖而感到腦力耗竭。但腦力耗竭並不是一個事實,而是大腦發現了有能量消耗的情況發生,並「預測」是否要節約能量。長年下來,如果已經習慣「啊!好難!算了好累。」大腦就會累積經驗並在下一次更容易預測出耗竭結果。但我們可以透過回想,試著創造新的故事「雖然很難,但快成功了,這種感覺是當時的我正在燃燒。」便有機會在下一次相同情境時有不一樣的預測。
其中也呼應這一系列探索的起點:為什麼我們難以抽身於焦慮 所提到的反芻與反覆思考。我們一樣要小心地選擇,選擇我們希望融合的新概念,避免反芻強化負向信念。而這些概念隨時間與不同情境回想、建構記憶。
最終概念,就是我們的經驗複利。
小結
大腦在預測迴路中,運用概念預測、賦予意義,如果經歷「經驗盲區」就會如上圖的噪點。但一旦看到下圖經驗了,就會意識到這是蜜蜂的黑白圖像:

當我賦予噪點「蜜蜂」的概念時,注意到了噪點的邊緣成形為蜜蜂特徵的形狀,進一步啟動了「畏懼」情緒概念,引發身體產生肌肉緊張等預算狀態,繼而經驗了「畏懼」。
我曾困惑:如果一切都是由個人預測並賦予意義,那世間不幸,都是歸咎於個人嗎?但重看上圖,我卻無法重複經驗盲區的未知狀態,因為噪點已有了意義。這讓我察覺概念建構在「責任」上的矛盾之處,而 《How Emotion Are Made》 給出了精巧的責任論:
「責任」就意味著做出審慎的選擇,改變自己的概念。
回到我最常思考的「真實」,從情緒建構理論,我得審慎選擇會吸收到什麼「概念」,因為這些「概念」會決定了未來的我會經驗什麼樣的「真實」。
本文感謝 Parker, 翰元 與 雅瑄 閱讀初稿與建議。也感謝大家的閱讀 🙏 如果文章中有任何需要修訂或喜歡的地方,歡迎都可以留言告訴我。
參考資料
Footnotes
-
在概念預測前,鼻周皮質會先初判感知到的刺激,是否有匹配的概念。實驗發現,當電極刺激鼻周皮質時,會引發受測者的「似曾相識」感,卻無法具體描述熟悉的內容。例如,當感知到綠色、紡錘形薄片,鼻周皮質便會想:「嗯!這東西好像認得。」初步判斷後,鼻周皮質會將結果訊號傳給前額葉皮質,以決定進一步提供概念或提升注意力來釐清。 ↩
-
當前額葉皮質收到鼻周皮質的訊號後,便會搜尋適合的概念進行預測,賦予感知意義。例如,看見綠色紡錘狀薄片時,我們認出它是「葉子」,並自動聯想到「葉子通常長在植物上」等延伸概念。前額葉皮質在概念化時,也會判斷此問題是否只需概念即可解決?如果概念不夠,還需要海馬迴來提供過去經驗補充。 ↩
-
前額葉皮質會調用海馬迴來重建事件記憶,假如現在多了一個目標概念:「分享最漂亮的葉子」。光靠概念還不夠,前額葉皮質需要「曾看過的最漂亮葉子」的記憶協助。於是找了存放情境模型的海馬迴,提取出「有人」、「公園」、「去年」、「公園葉子」的情境。最後,前額葉皮質將概念與情境結合,形成完整的事件記憶:「去年與朋友在公園看到的葉子」大腦再依此持續調整預測,完成目標。 ↩
-
在 《The Body Keeps the Score》也提到相當多透過非語言來表述概念的療癒案例。 ↩
-
想到在 《The Book of Human Emotions》中列舉了很多只有各國語言才有的情緒,例如,日文中的物哀,便是對物換星移移情的傷感,但這是在中文沒有直接對應的概念。 ↩